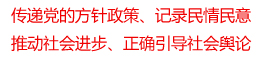|
作为一名老新闻工作者,我对沁阳的烈士情况颇为了解,可那天中午,我在沁阳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却遇到一位老人在咨询其父作为烈士能不能迁入烈士陵园的事,十分震撼。 老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敏感和对探索完善沁阳革命历史进程的强烈责任感,使我决定找老人来个追根求源。 老人说,他叫田趁上,1943年生人,家住沁阳市西万镇和庄村。父亲叫田小虫,是西万镇西万村人,1944年和其他6个人一起被害,经过组织上的多年调查,直到1990年才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父亲是西万人,他却是和庄人,1990年才认定为烈士,其中必有故事!我决定深挖下去,没想到我的这一坚持竟揭开了沁阳一桩鲜为人知的惨案,还原了一群鲜活的革命英雄群体。 一 这天下午,田趁上和一位老太太来找我。老太太说她叫任玉芳,1941年出生,娘家是西万镇道口村,父亲叫任清泽,和田趁上的父亲同一天被害。今天田趁上来找我谈此事,也一道叫上了她。 田趁上跟我谈了他所知道的关于父亲的情况。他说,听老人们讲,父亲当年先跟着田时风干,后来跟着董学义干。1944年秋天,董学义派他们到窑头设卡站岗,任清泽是班长,一天,被沁阳城里派来的伪军给打死了,丢在废弃的煤井里。 父亲死时,他才9个月大,半年后,母亲也死了。由于1946年土改时,父亲被认定为伪军,他成了“被杀伪军家属”而受到冲击,原来分在他名下的土地和房屋也被分给了别人。1955年祖母去世,他一人生活艰难,后经人撮合过继给和庄村的一户人家,这才落户到和庄。 任玉芳也说,父亲死时她才两三岁,也因为被定为“被杀伪军家属”在道口村倍受歧视,不得已后来到景明村跟了自己的舅舅。 二 他们介绍完,我问道,你们父亲死时,你们都那么小,怎么知道自己父亲是干革命的,而不是伪军? 田趁上说道,小时候背上“被杀伪军家属”这个罪名可遭了罪了,在他幼小的心灵里一直想摆脱这个罪名。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起,他就一直想弄清楚父亲到底是怎么死的。可他得到的答案大多数是,他的父亲是伪军之间狗咬狗被打死的。就在他垂头丧气时,西万村的董学锋对他说:“我听说你父亲是搞地下工作的。你慢慢打听知情人就会知道的。” 1973年春节的大年初五,他听说西万村的老革命,当时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任党委办公室主任的田泽普回乡探亲,便前去打听。 田泽普听了他的陈述后沉思良久,最后说,他的父亲田小虫确实是地下工作者,并说,与他父亲一起被害的共有7人。 田趁上听后非常激动,想着这些年来受到的不公待遇,又问道,当时为啥不确认他们为烈士? 田泽普叹口气说,当时不能呀!如果那样做革命就会受到很大损失。 接着田泽普又说,现在知道这个事的人不多了,我一个,雷起云一个、田绍松一个、马子明一个,得赶快调查取材料。你个人不行,得组织上去调查取材料。说着,田泽普一一把他们的工作单位和住址写下来交给田趁上,让他交给组织去调查取证。 后来,组织上经过反反复复的调查,直到1990年,他的父亲才被批准为烈士。 三 田趁上介绍完,任玉芳紧接着说,当时与她父亲一同设卡站岗的有8个人,死了7个,跑了1个。跑的这个人叫郭福喜,是常平乡窑头村人,这个事情发生后,他就回了部队,接着随部队南下,后来在战斗中负伤,失去了一条腿,是一名光荣的伤残军人。她曾多次见过郭福喜,郭福喜也曾给她讲过事情发生的经过—— 这事发生在1944年的农历八月初六,当天他们8个人被抓住后,敌人审讯他们,问他们谁是你们的领导。任清泽说,我是领导。敌人又问,你的领导叫什么?在山上哪儿住?任清泽一拍胸脯说,都在我这儿,就是不给你们说。大伙没有一个人透露实情,敌人见审讯不出来,准备下毒手,郭福喜见状对敌人说,我不知道我们的领导叫啥名,但我知道在山上哪里住,晚上了我把你们领上去。 敌人听信了郭福喜的话,半下午时,就让他带路往山上走。郭福喜凭借着自己是窑头人,对窑头的地形熟悉,走上路,就钻进路边的玉米地跑了。可他没跑远,仍趴在附近的山头查看敌人的行踪。天快黑时,敌人把这7个人捆住拖出来,分别扔到了废弃的煤窑井里。他见大家都牺牲了,就赶快去找部队了。 田趁上与任玉芳还说,他们父亲被害后,七家人相约往山上找,找到第七天时,在山上见到一个放牛的,一问,人家说,前几天有伪军狗咬狗打死了几个人都丢到煤井里了。找人捞上来一看,就是他们。他们手和脚被绑在一起,脖子上套着绳子。七天了,尸体都发胀了。 从1973年开始,他们就一直向组织反映。组织上也一直在调查,光调查材料就写有一尺厚。1990年,烈士证书终于发下来了。当时,有人说,你们都这么大了,也享受不了什么烈属优待了,还找什么找?他们回答说,在他们心中本来就不是为了优待,主要是为了给老人们一个交待,揭去背在他们身上几十年的黑锅。 四 送走两位老人,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发生在沁阳土地上,一次7名地下工作者被害的大惨案,有关地方党史和市志竟从来没有记载过,真的很遗憾。那么,他们说的情节是不是真的,与当年的调查结果是不是相符?如果是真的,是什么原因事情过去多年,竟没人提起? 面对这些疑问,我觉得我这个老新闻工作者有责任来厘清事实。如果是真的,我有义务有责任来还原这桩惨案,让更多的人知道英雄的事迹。 根据两位老人提供的线索我进行了认真的梳理。两位老人所提到的田时风,也是我党的地下工作者,1940年4月,任太岳军区二分区敌工科副科长,并兼任沁济抗日民主县政府县长。1943年12月被敌伪军包围壮烈牺牲。董学锋,我曾于2011年采访过他,知道他也是我党领导下的沁阳抗日县大队的成员。其他同志只是在沁阳有关党史的书籍上见过他们的名字,情况不太熟悉。怎么办?我决定从拜访老同志入手。 我先给焦作市军事志专家吉怀儒同志打电话,问他知不知道这个窑头惨案。他说,从来没有听说过。不过,当时我党在西万与敌人争夺得比较厉害,田时风、田泽普、田绍松等都是我党的地下工作者,董学义原来确实干过伪军,1942年10月底被我党争取过来,也从事地下工作,1946年被错杀。 又打电话给沁阳市民政局退休干部牛庄起,询问当年调查此事的情况。他说,时间太久了,刚开始田趁上他们反映情况时,他才刚参加工作。当年向上申报烈士时,用的是沁阳县人民政府的名义,记得这些档案都已经移交给沁阳市档案馆了。 五 在沁阳市档案馆,我还真的查找到了沁政(1988)5号,名为《关于追认任清泽等七位同志为革命烈士的请示》的文件。 从这份文件中得知,任清泽、田小虫、宋小会、赵麻刚、赵小挡分别是1939年、1940年、1942年在太岳军区二分区参加革命的老八路;而杜小树、刘小兰则是分别于1944年2月与6月先后参加我党领导的地下武装伪自卫团,从而参加革命的。 他们的被害经过,文件中是这样描述的—— “经过调查确证,任清泽、宋小会、田小虫、赵麻刚、赵小挡等五位同志均属我八路军太岳军区二分区成员,一九四三年,他们受上级指派,随董学义同志下山到敌占区做地下工作,为隐蔽身份,成立了一个‘伪自卫团’(地点在沁阳县西万乡西万村,杜小树、刘小兰后也参加了这一组织),在敌占区开展抗日武装斗争。一九四四年五月,受董学义委派,这支地下武装由任清泽带领一个班,在解放区(山上)与敌占区(山下)的交通要道——沁阳县常平乡窑头村外上楼设‘厘金卡’(实际上是‘护路站’,即我八路军的联络站),以收路税为名,秘密进行抗日工作,负责护送过往八路军干部,保证我八路军山下与山上的联系与通道安全。 一九四四年八月的一天,日伪汉奸……为争夺这个交通要道,派了一个连的兵力,秘密包围了窑头村……将任清泽、宋小会、田小虫、赵麻刚、赵小挡、杜小树、刘小兰等七人捆绑后拴在一起,强令他们全部脱掉鞋子,押往窑头村西南方的方山下,用绳子一一勒死后,全部丢入了该处的一口废煤窑井内。” 根据这些事实,最后文件要求追认任清泽等七位同志为革命烈士。 六 这个文件虽然记录了事情的经过,但对于我这个老新闻工作者来说,这样的结果并不能让我满足,一是具体细节还不够完善;二是为何党会派任清泽这些老革命,跟随1942年10月底才刚刚被争取过来的董学义下山开展革命工作呢? 带着这些疑问,我用一个多月时间,认真阅读了中共沁阳市委党史研究室、1998年编撰出版的大型沁阳党史文集《风雨征程·1919—1949》,从马子明(从1943年春起先后担任中共晋沁县委副书记、代理书记兼抗日县大队政委)撰写的《抗日战争时期晋沁地区的革命斗争》、田泽普(从1942年2月起在沁阳、博爱一带做地下工作)撰写的《我沁(阳)博(爱)地区地下武装建立的前前后后》及其它如《我敌工人员策反西万伪军起义前后》等回忆文章及资料中,慢慢理出了头绪。 沁阳西万镇地处太行山南麓,是河南通往山西的咽喉要道。日军侵占豫北后,原土匪、博爱县伪军二十一师所属常世元部盘踞西万,阻断了太行山抗日根据地与山下的交通。 为了策反常世元,从1940年开始,太岳军区先后派尚有明、田泽普、田新华等下山打入常部,设法接近常世元和他的贴身警卫董学义,启发他们弃暗投明。为加大策反工作力度,1942年4月,太岳军区在晋城的范河村成立了“晋南敌工站”,后改为“晋沁敌工站”,对外称“八路军办事处”。太岳二分区敌工科副科长田时风兼任站长。 后来,常世元部在起不起义的犹豫中被日军击溃。1942年10月21日,董学义带领200余人成功起义,被改编为“沁阳抗日县大队”。但由于一些起义人员吃不了苦、受不了八路军纪律约束,出现了叛逃现象。太岳军区便将计就计,派董学义也以叛逃名义下山,打入敌人内部做地下工作。 董学义下山回到西万后,很快掌握了西万自卫团,并用计取得日军的信任,被正式任命为日军宪兵队便衣队队长,活动在沁阳、博爱一带,为我党、我军搜集情报、筹集军用物资、开展地下工作立下了汗马功劳。 1944年春,窑头山口不断发生劫路杀人事件。这不仅危及群众安全,也严重威胁着经窑头来往于山上山下我过往干部的安全。在晋沁敌工站的指示下,董学义在窑头山口南端设立护路站,名为“厘金卡”,保证我过往干部的顺利通行。 七 根据这些资料抽丝剥茧,我渐渐解开了心中的疑团—— 任清泽等这些老八路,就是1943年以叛逃名义跟随董学义下山打入敌人内部,协助董学义在敌人心脏开展革命工作的我党骨干地下工作者。1944年春天以后,他们就受命在窑头村口以设卡的名义保护我过往干部的安全。后来,敌人对这个“厘金卡”产生怀疑,便用计拔掉这个关卡,任清泽他们也因此遇害。 为什么一次牺牲七个同志这样大的惨案,随后就湮没在人们的记忆之中了呢?原因大概有二: 一者,正如田泽普对田趁上所言,如果当时承认他们是烈士,“革命就会受到很大损失”。试想,如果我党当时公开承认他们是烈士,董学义的身份就会马上暴露,不仅他及许多同志都会因此丢掉性命,而且我党苦心创建的山上山下通道就会被掐断。 二者,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内战接着爆发,安排他们打入敌人内部的敌工站领导干部,都随部队纷纷南下,千里转战,很少再有回到太岳根据地的。要不是老家在西万村的田泽普1973年回乡探亲,此事很可能就会完全沉寂在历史的长河中了。 正是由于以上这些原因,才使任清泽等七位烈士在等了近50年的时间后,才拿到了迟到的烈士证书。 八 当我把梳理结果拿给沁阳党史办负责同志看时,他连说,想不到沁阳还有这样鲜活的地下工作者!当我把梳理结果告诉田趁上、任玉芳两位老人时,他们连声道谢,说这是在给他们的父亲立传呀! 我问田趁上老人他的父亲现葬何处?他说,当年从废煤窑井中捞出父亲的尸体后,家人就把他丘在了西万到窑头的石河边上。那些年,他没有能力把父母合葬在一起。自打父亲的烈士证下来后,压在他心头的石头搬开了,经济条件也好了,1994年他终于把父母合葬在一起,让他老人家入土为安,并没有进入烈士陵园。 听着这些话,我在感慨万千的同时,也很欣慰自己作为一名老新闻工作者能在与田趁上老人的一次偶遇中,还原了一段记载缺失的历史,为后世找到了一个鲜活的英雄群体,让英雄的英名不再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